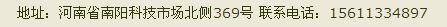脑洞大开人间有味是清欢,居然说的是这种
眼下这个季节,正是芦荻花开的季节,加上水蓼也开满了红花,红红绿绿的背景,能拍摄到好看的大片。
水蓼是名副其实的野草,农民眼里最不能容忍的野草。小时候在水边经常看到这种野草,割草的时候会毫不留情地一刀搂一把。每年的4月和5月,正是它们疯狂生长的季节,一天能长1-3厘米。如果不行张在秧田里,那水稻可就遭殃了,它会发展成一种疯狂的侵略者,让可怜的水稻被吃掉。对待稻田里、田埂边的水蓼,我是不用镰刀的,而是连根拔起,扔到水槽里去。
今天晨会,记者报选题,说到这种被视为杂草的植物,是《诗经》中的宝贝。于是唤醒了我儿时的记忆,也让我长了知识。
我一直不知道它还是一味草药。看来,这么多年,我误会了它。水蓼具有滞湿、散瘀、止血、祛风止痒、解毒的作用。用于湿性迟滞性耐药,常出现腹痛、腹泻、痢疾、小儿营养不良等产品,经痛、血瘀闭经、痛经、外伤、风湿痹痛、血瘀、外伤性出血、皮肤瘙痒、湿疹、风疹、足癣、痈肿、蛇咬等。凡事都要量力而行,过犹不及,一旦剂量太大,就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多的水芹有毒,会引起心痛。
头上长了疮?脚肿了?扭曲?蛇咬伤?当面临这些问题时,农民们总是希望尽快在水边找到水蓼。特别是被蛇咬伤后,用手拿水蓼,用石头或用嘴(紧急时,通常用嘴)将水蓼咀嚼后,敷在伤口上。
古代文献中单称的蓼大多指的是水蓼,当然也有可能指称其它蓼科植物。《诗经》中有两处提到“蓼”,一首为《周颂·良耜》“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另一首为《周颂·小毖》“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前一首介绍农事,说拔除“荼(tú)”和“蓼”这两种野草,沤烂在田地里做肥料,可使农作物黍稷生长茂盛。后一首是周成王自我警戒以求群臣辅佐的诗,“蓼”在此处指“辛苦之菜”,比喻治国理政之艰辛。南朝时陶弘景称蓼可食者有三种,一为紫蓼,“相似而紫色”。二为香蓼,“亦相似而香,并不甚辛而好食”。三为青蓼,“人家常有,其叶有圆者、尖者,以圆者为胜”。
苏轼《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一词载有以“蓼茸”作春盘的吃法: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诗中“南山”亦现在江苏省盱眙县的第一山,说明宋代水蓼已是常见的一种野菜,在江淮地区被普遍食用。
“蓼茸蒿笋”这类普通的野菜,也可为时令之佳肴。心境不一样,粗茶淡饭也是人间至味。水蓼嫩苗究竟是什么味道?我从未吃过,我的邻居也没吃过,菜市场似乎也没有见到。哪知道水蓼是中国古代除了黄豆芽、绿豆芽之外,最早用于培育芽苗菜的植物,并且是最早记载的一种人工温培芽苗菜。
还有人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其实是“卧蓼尝胆”,典出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越王念复吴雠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目卧”是打瞌睡的意思,晚上犯困了,就用“蓼”这种辛辣之菜来刺激眼睛,以保持清醒。越王勾践这般励志刻苦,应该可跟后世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相媲美。
转载请注明:http://www.kofkh.com/wahl/141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