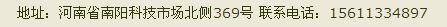法经监管信息型市场操纵的内涵与外延基于行
市场操纵依手段不同可划分为交易型、行动型和信息型操纵三类。我国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表明,信息型操纵作为一种新型且隐蔽的操纵手法在近两年呈多发态势。信息型操纵是指一切通过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欺诈其他市场交易者,对他们产生误导效应,人为改变市场上正常的供需关系,对证券交易价格和/或证券交易量造成扭曲,借此牟利的行为。我国信息型操纵包括抢帽子交易、蛊惑交易和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三种。在认定抢帽子交易时,行为人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和行为的欺诈属性是核心问题;我国目前尚没有蛊惑交易操纵案例,是因蛊惑交易在法律上很难构成,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显得尤为必要;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中的信息优势是指能够获取、了解、主动制造、拆分、加工、发布、传播各类重大信息的优势,这类行为与内幕交易、虚假陈述行为存在诸多竞合,亟待从法律上加以明晰。
本文原发于《证券法苑》第21卷,由我们的好朋友,北京市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瑶撰写。由于篇幅较长,我们分为上下两篇推送给大家,本篇为下,介绍信息型市场操纵的特征以及结论。
五、信息型市场操纵的特征——相较于虚假陈述、
内幕交易、编造传播虚假证券信息行为
信息型操纵行为与内幕交易、虚假陈述因为都涉及对信息优势的滥用,在认定上难免存在竞合的问题,如何划清其中的界限,避免一个行为产生多个处罚结果,是监管层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由以上讨论可知,信息型操纵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存在诸多竞合,如,蛊惑交易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如何区分?抢帽子交易与内幕交易如何区分?上市公司高管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买卖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如何区分?私募机构与上市公司高管配合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买卖与内幕交易如何区分?此部分将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并从中凸显信息型操纵的特征。
(一)信息型操纵与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或者不当披露的行为。”虚假陈述的主体是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发行人及上市公司,行为的类型包括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以及不当披露。
虚假陈述与信息型市场操纵都是证券欺诈行为,在信息型操纵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的手段完成时,二者可能存在竞合的情况。但是,虚假陈述的主体范围非常小,仅限于发行人和上市公司,因此,只有在涉及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行为中涉及高管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公司发布信息时,二者才存在竞合的可能,而在此种情况下,二者要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合还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信息的内容属于披露义务的范围;二是发布信息的性质要满足虚假信息中的虚假或误导属性。实践中,上市公司高管利用上市公司这一平台发布的信息往往是不具有“重大性”的信息,甚至是一些不必要发生或不必要披露的信息。就信息本身来说,可能是虚假的扭曲的信息,也可能是基于真实而夸大或拆分的信息,甚至可以是完全真实的信息。
以一个不是特别重要但可控度非常高的利好消息,如开展高送转方案为例,哪怕公司的业绩并不好,也可以决定实施高送转,并且如果最终真的实施了,就不能认定其构成虚假陈述;以一个特别重要但可控度非常低的利好消息如并购方案为例,虽然最终未能实现,但是由于是各种不可控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对前期进展的披露如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也不能认定其构成虚假陈述。
以朱德洪案为例,若不是高管高位减持股票套利的意图明显,使该案被认定为操纵市场无疑,案件中涉及的不法行为完全有构成虚假陈述可能:朱德洪寻找并购重组题材和热点,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很可能涉及到虚假陈述(隐瞒应当披露的事项),当然,并购作为一项极具商业风险的活动,成败与否由多种因素如市场环境、政策执行等决定,不受公司的控制,属于低可控度事项,在并购重组各方意向谈判阶段,公司也不存在强制信息披露的义务,因而构成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也可能存在整个并购重组计划都是虚构的情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重组的计划和意向,或根本没有进行重组的实力,行为人为拉抬股价配之以相应信息披露的节点和内容,则构成虚假陈述。对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区分就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比如,如果大股东、高管及关联人事先有减持痕迹,那么这样的信息披露很可能就是虚假的,因为交易的意向(卖空)与标的证券的价格走势(因利好消息而上涨)呈不合逻辑的反向关系,则足以引起怀疑。
而行为如果已经构成虚假陈述,则涉及虚假陈述与操纵市场竞合的问题。从刑法理论上来说,对于这种手段与目的的竞合,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就两种行为间的关系来看,虚假陈述只是手段,起辅助作用,操纵行为才是目的,起主要作用。但是,两种行为又可以独立存在,分别构罪。所以,如果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这两种犯罪行为,应该以数罪并罚处理,如果证据只能证明某一种犯罪行为,就只能按照一罪来定罪处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情形属于手段牵连,应依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论处,不宜数罪并罚,并且认为,如果在实践中只能查明虚假陈述行为,无法充分证明操纵目的时,则应以虚假陈述来进行处罚。
本文赞成第二种观点。此类操纵行为的本质还是对证券价格和交易量的扰乱,而不是对信息披露制度的违反,如果采用并罚的方式可能有失公允,原则上应以市场操纵进行认定,在证据不足时,可以认定为虚假陈述,作为一种兜底的处罚措施。
另外,如何避免行为人通过真实信息的披露操纵市场也是未来监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种行为因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而脱离了虚假陈述责任范围,从而在实施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以大股东为了减持股票和开展的“高送转”方案为例,这类信息本身是真实的,最终也确实会落实,但行为本质上是为了拉高股价为减持作准备,虽然不能构成虚假陈述,但完善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确有必要。在未来,或许可以考虑要求上市公司在发布“高送转”等非内幕信息但又确实对投资者有一定影响信息的同时,要披露公司业绩情况或者大股东减持计划,以尽最大可能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二)信息型操纵与内幕交易
在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型操纵中,由于行为人大都属于具有信息优势地位的内幕人,掌控诸多内幕信息,有的甚至是内幕信息的源头制造者,使此类行为极易与内幕交易相混淆。
以徐翔案为例,根据新闻报道的描述,人们会产生到底是涉及内幕交易还是操纵市场的疑惑。而实际上,官方先前发布几次信息也确实认为徐翔涉嫌内幕交易罪和操纵证券市场罪两个罪名:年11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年4月29日,新华社电文再次提到“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犯罪”。这次电文少了一条“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但仍有“内幕交易犯罪”的表述。直到年11月10日,青岛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时的表述是“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系列案”,没有提到涉嫌内幕交易罪。
操纵市场行为的本质是欺诈,是一种滥用资源优势损害他人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但其违法性的关键不在于涉及哪一种具体的资源优势,而在于行为是否反映操纵的本质,即借助某一或某几种优势连续买卖证券的外在形式背后,是否具有制造证券交易活跃假象或诱使他人跟风买卖证券的主观动因。具体到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对信息优势的利用并不是该违法行为的本质特征,内幕交易中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同样具有信息优势,其利用内幕信息的重大性和非公开性而抢先交易牟利,因而被认定为是内幕交易。因此,如果不对这两种“利用”信息的情形加以区分,则无法将内幕交易与利用信息优势的连续交易操纵行为区分开来。
内幕交易与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意图不同
这是二者之间最为本质的区别。内幕交易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利用未公开的内幕信息交易获利,其利用的是信息本身的“重大性”和“非公开性”,获利的来源是信息本身。而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通过对信息发布节奏和内容的控制,造成市场活跃的假象并吸引其他投资者跟风操作,从而达到获利目的,获利的来源是市场活跃假象和其他投资者的跟风交易,这在鲜言案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也就是说,内幕交易行为人主观上意图利用未公开信息获利,而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行为人则意图通过对股价的操纵获利。
以黄光裕内幕交易案为例,黄光裕亲自筹划了中关村的重大资产重组,并自筹划伊始就通过亲友开立了近两百个股票账户买入中关村股票,并在重组通过并公告之后陆续卖出股票获利,因该重组信息一经发布便会对股价产生影响,其在内幕信息形成之后公开之前买入、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后卖出,就会赚取相应的差价。
反观徐翔案,其对信息优势的控制(如指令高管发布“高送转”方案、释放公司业绩、引入热点题材等利好信息的披露时机和内容)仅仅是其达到操纵股票价格的手段,在这些信息发布之前或之后,其所实际控制的泽熙产品证券账户、个人证券账户会择机进行相关股票的连续买卖,达到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虚高,使得徐翔等人可以在高位抛售股票获利。也就是说,本案的信息型操纵市场所依靠的不仅仅是信息优势本身,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还有资金优势的配合,这样才足以达到行为人主观上通过对股票价格进行操纵获利的意图。
2.信息的本质不同
信息型市场操纵中的信息并非一定具有内幕信息所具备的“重大性”,甚至是一些不必要发生或不必要披露的信息。
“重大性”和“非公开性”是内幕交易中内幕信息所必备的两个特点,其中“重大性”是指该信息重要到足以能够影响正常投资者的投资判断和决策。证券法列举的内幕信息有订立重大合同、增资计划、股权结构重大变化、重大诉讼等。这些信息依《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当属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的事项,也就具备了在披露之前禁止交易的必要。这些信息多为表决产生而非一人、几人所能控制。
而在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中,行为人本身在多数情况下就是消息的制造和谋划方。对于其所进行的信息披露,有些披露是不必要的,如一些业绩并不好的公司也可以发布公告开展“高送转”;有些信息则是不需要披露的,如热点题材、概念等。通过对这些信息发布的内容和节奏的控制,行为人可以吸引投资者跟进操作,或者配以资金炒作吸引投资者跟风操作,进而反向操作获利。
3.主体不同
内幕交易行为人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而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的行为人是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关联人等对信息的发布有一定控制能力的人员。
以朱德洪案为例,朱德洪作为标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掌握具体收购计划的详细进程并泄露给从事“市值管理”的上海永邦,这本身是一个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若上海永邦利用这一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则有内幕交易之嫌,具体到实践中,监管机关可能面临的难题是,要证明上海永邦知悉并利用内幕信息,也就是要符合内幕交易的主体构成要件。同时,上海永邦交易的时间点也要严格符合内幕交易的行为构成要件——即在内幕信息形成后、公开前买入,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显然,对这种行为的证明一方面比较困难,另一方面,若交易的时点不能对应,则要么行为人并无利用内幕信息获利的意图,要么由于监管监测的先进性,行为人有意而避之,但从交易的本质来看,高管高位减持股票的意图已经说明了其与私募机构合谋操纵的意图,因而构成操纵市场的可能性更大,在认定上也更为合理。
4.违法、犯罪构成不同
内幕交易属于行为犯,有相应行为并达到立案追诉的获利金额即构成违法、犯罪,而操纵证券市场属于结果犯,只有对证券交易价格和证券交易量产生一定影响、达到一定标准的才构成违法、犯罪(亦有人认为操纵证券市场罪属情节犯,即,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违法、犯罪)。
(三)信息型操纵与编造传播虚假证券信息
国外语义下的信息型操纵是指,以散布、传播虚假信息、谣言为基础进行的引诱其他市场主体进行交易从而获利的行为。我国语境下的信息型操纵与此界定不完全一致。相反,对于散布虚假信息和传播谣言扰乱证券、期货市场的的行为,我国以《证监会指引》中的蛊惑交易和《刑法》第条“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证券法》第78条“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来规范,至于我国为何采纳这样的规制方式以及这样的规制方式是否合理,可以通过将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行为与信息型操纵中的抢帽子交易和蛊惑交易行为相对比而得出。
从体系上来看,关于抢帽子交易和蛊惑交易的明确界定只出现在内部执法文件《证监会指引》当中,该指引相当于是对《证券法》第77条的解释和细化,在该指引中,抢帽子交易和蛊惑交易属于《证券法》第77条第1款第4项的“其他手段操纵市场”,那么,按照证监会的思路,这两类操纵至少要具备一般市场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操纵的故意、行为人从事相关交易、行为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或证券交易量造成影响等。另外在主体要件上,抢帽子交易的主体只能是证券专业人员等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人,而蛊惑交易的主体则为一般主体。而《证券法》第78条针对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传播媒介从业人员、证券专业人员、工作人员等一切能够传播证券信息的传播媒介,规制的是这些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产生信息误导,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二者最为本质的差别在于,《证券法》第78条不要求交易的发生,单纯的信息发布与传播行为即可构成。
从执法实践来看,在目前为止证监会用《证券法》第77条第1款第4项兜底条款做出的处罚里面,没有一起构成蛊惑交易的案例,但是以《证券法》第78条做出的关于编造传播虚假证券信息行为的处罚确实已经有一些(截至年3月共计15个)。实际上,按照《证监会指引》的认定思路,蛊惑交易在法律上是很难构成的,作为一般主体的操纵人,即便基于操纵市场的意图编造、传播了虚假信息,要么没有发生任何交易,要么有交易但是行为未对股市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些情况下,《证券法》第78条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兜底条款对这些行为进行规制。
具体而言,蛊惑交易就是指,行为人借助于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利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不确定的重大信息,诱导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自己趁机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行为人为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实现获取利益或规避风险的目的而实施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应当如何处罚?
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在大部分国家是作为操纵市场犯罪的一种行为方式来进行定罪处罚的,我国在刑法修订中将这一类行为从市场操纵罪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种犯罪予以规定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信息型操纵行为中,行为人利用的信息多为真实的或相对准确、完整的信息,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中的信息是虚假信息,将两个行为单独立法有利于对违法行为的全面打击;第二,市场操纵往往难以与正常交易行为相区别,但如果操纵者存在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的行为,或是以此为手段进行的操纵,可以此行为定罪处罚,对监管者而言,证明难度大大减小,有利于监管的开展。
如果两种行为都能够满足各自的构成要件,则确有竞合的问题,如何处理应当采用前述竞合问题适用的理论,但是,蛊惑交易操纵能否在法律上成立是先决问题。按照《证监会指引》的规定,蛊惑交易操纵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发布虚假信息;其次,行为人发布的虚假信息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从而对证券交易价格或证券交易量产生影响;再次,行为人要有证券交易行为,即:在信息发布前买入或卖出,在信息发布后从事反向交易;最后,行为人的目的是通过信息发布对股价的影响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其他类别的信息型操纵,蛊惑交易的主体就是一般主体,任何人实施这样的行为均可构成该类操纵。但问题在于,对证券价格或证券交易量产生影响的市场操纵行为一般要么来源于行为人的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要么来源于行为人的市场影响力,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想通过简单的发布虚假信息行为对市场造成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般人在市场上散布虚假信息,并寄希望于通过这种虚假信息影响其他人的投资决策和判断从而影响证券价量获利的可能性也不大,市场上的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往往源自于行为人博眼球的心理,而不是通过交易获利心理,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影响方面,蛊惑交易在法律上都很难成立,这也是近年来实践中无一实例的原因。那么,在证据缺失、法律上蛊惑交易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应以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定罪量刑或依据《证券法》第78条关于编造传播虚假证券信息行为进行处罚。因为,不管基于何种目的,虚假信息的散布对市场的扰乱作用是显著的,甚至可能会浪费很多市场资源——涉事公司一般都不得不出面对此问题进行澄清,以降低或消除公众的误解,因而,此类行为的规制也是必要的。在蛊惑交易不能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证券法》第78条“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的规制缺失,则对此类行为的放任必定会造成证券市场上的混乱,因此,此条设置很有必要。
六、结论
我国操纵市场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初步表明,操纵行为人的违法手段正呈现多样化趋势,信息型操纵占比较高且呈上升发展态势,亟待引起立法层面上的重视。从目前的监管实践来看,证监会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对信息型操纵的监管思路,基本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违法行为,但在处罚的依据以及处罚的证明及说理上仍存在较大的欠缺。
从立法体系上来看,我国涉及信息型市场操纵(包括抢帽子交易、蛊惑交易、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和编造、传播虚假证券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的条文分落在《刑法》第、条、《立案追诉标准》第37、39条、《证券法》第77条第1款第1、4项、第78条以及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证监会指引》当中。就我国目前的市场形势而言,信息型操纵手段的丰富性使得就信息型操纵进行的立法很难形成体系,但是,通过对其中涉及问题的一一分析,至少能厘清此类行为的一些本质特征,使我国未来即使依然采用散落式的立法模式,也能让各个条文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更加明确,不至产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模糊或错误。
在抢帽子交易案件中,行为人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和行为的欺诈属性是其中两个核心问题,具有市场影响力的证券专业人员和财经专栏记者、博主等人在发布荐股信息之前从事证券交易,在发布信息对市场产生作用以后从事反向交易获利,即是对实际或潜在客户信义义务的违反,构成抢帽子交易操纵市场。
蛊惑交易中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这类行为人即便基于操纵市场的意图编造、传播了虚假信息,却没有发生任何交易,或是有交易行为但信息发布不足以对股市产生任何影响,因而在法律上很难满足蛊惑交易的构成要件,蛊惑交易条文的设置(目前仅出现在《证监会指引》当中)也就显得有些不必要。这类行为虽然没有对标的证券价格造成扰乱,但虚假信息的散布对市场仍有一定扰乱作用,甚至会浪费很多资源,因此应以“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进行规制。
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交易中的信息优势是指能够获取、了解、主动制造、拆分、加工、发布、传播各类重大信息的优势,在这类操纵中,行为人不单是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股票交易期待通过信息公开后的股价波动赚取差价,他们同时还人为地扰乱了市场上信息和价格的关系,使股票价格不能成为市场上所有信息的有效反映,这是其与内幕交易行为的根本区别。因此,此类操纵模式与内幕交易本身并不是竞合关系,而是可以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表现和主观意图不同作出根本性的区别判断。在利用信息优势时,行为人除了向公众发布诱导性信息以外,还可能隐瞒真实信息,甚至通过篡改一些事实证据来实现干扰市场的目的,因此,在此类操纵行为中还存在是否同时构成虚假陈述的手段与目的牵连竞合问题。本文认为,在同时满足虚假陈述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应以目的吸收手段认定为市场操纵为宜,不宜数罪并罚或认定为多个行为分别处罚。
当下操纵市场监管最重要的任务是能够将一些细化的条文在《证券法》的修订中有所体现,结合证监会已有的执法实践、国外理论研究和国内业界讨论,将操纵市场行为尤其是信息型操纵尽可能做出穷尽性的类型化划分并配之以相对明晰的法律条文、司法解释,以赋予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坚实的法律依据,去除执法过程中对《证监会指引》这一内部指导文件的依赖;同时,也给市场主体带来更多的确定性,以在违法行为与商业合理性之间寻求适当的边界。
本文作者:徐瑶
法经笔记声音
热干面,你要好起来啊!
创办于年5月,这是第篇原创,主要栏目有:
:立足前沿,
转载请注明:http://www.kofkh.com/wazz/11571.html